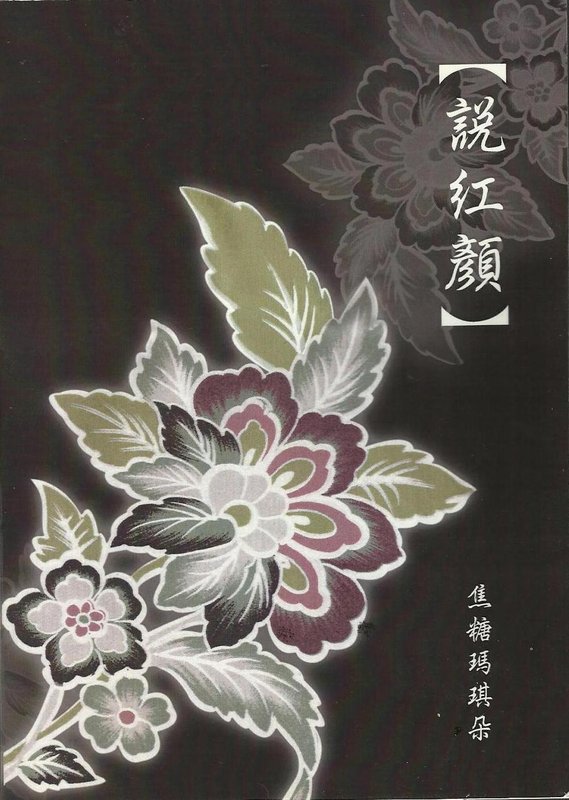
「我不怕,你倒怕了嗎?」
就為著這一句充滿挑戰性的話語,和她眼裡似訕似譏的笑意,沖田鷹司一頓之餘,尾隨在荻神官身後跟著老丈入屋。
風雪吹刮,漫無邊際的大雪原難見人煙,此間木屋十分簡陋,又少有外客,是以僅有灶間、老丈炕房和老丈義子之房。義子不在,兩人權且擠在只有一炕一几的狹小隔間。
荻神官一屁股坐上已燒得暖熱舒服的炕上,看著靜立在離炕最遠角落的沖田鷹司,低沉的聲音笑道:「就是要用激將法激起東瀛男兒的好勝之心,你才能排開這男──男之防嗎?」
沖田鷹司沒有回話。他進來,為的不單是什麼臉面。
「站著多累,過來坐下吧,也暖。」炕子有一人之長,想他面皮薄,她仍是往旁挪了挪,挪出可再坐三、四人的空間。
沖田鷹司道:「不用。」有種負氣的意味,卻不知是氣什麼。簡短二字隱約聽得出異國腔調。
荻神官嘿地一聲,炯亮得驚人的眼眸含著莫名笑意,「身為一個男人,卻如此小家子氣。」
沖田鷹司橫了她一眼,舉步到炕邊坐下。老丈這時端了一盤油黃包子入房來,說道:「茶淡菜疏,沒什麼好招待的,這幾個油炸肉包希望兩位不要嫌棄。」
「包子為何用油炸的?」沖田鷹司不解地問,一開口,外地口音更是明顯,聽著有些彆扭,又有些逗趣。
縱已聽了一段時間,荻神官仍是忍不住揚起嘴角,老丈年紀大了卻聽不出來,解釋道:「雪原上冷,蒸不出熱騰飽滿的包子,所以才用炸的。」
荻神官率先吃了起來,咬嚼之下讚賞地點點頭,對沖田鷹司道:「吃吃看,挺不錯的──」
沖田鷹司好奇地拿了一個,甫咬落,便被內餡滾燙的熱汁燙了舌。
「──就是燙了一點。」她笑著補充。
沖田鷹司瞪了她一眼,為了她那句刻意的拖遲。荻神官哈的一聲,笑得暢快。老丈又去倒了一壺熱茶讓兩人解膩。
「你真的不睡炕上?」荻神官問。
「不用。」沖田鷹司坐在屋角,背抵著牆。
「炕上暖和。」
「妳──炕上空間有限,妳該知道男女有別!孤男寡女共擠一床,成何體統?」微衝的語氣壓抑著。
「哈!你想到哪去了?」荻神官臉上是捉弄的笑,「我的意思是,你若要睡炕上,我就睡地上啊!講什麼成何體統,簡直比中原人還像中原人。」
沖田鷹司一陣語塞,臉上微起薄紅。
荻神官又道:「再說了,若真要談什麼禮防,不須共睡一床,同處一室已可構成罪名。」微冷微諷地睨著他。
「妳……我說不贏妳,妳睡炕上吧。」沖田鷹司無奈道。
荻神官率性地踢掉鞋子,躺上炕背對他,聲音傳來:「放心,我現下模樣不會引起誤會的。」
誤會?他不在意外人的誤會。
「你要休息時記得把燭火吹熄,」她又道:「亮著我睡不著。」
沖田鷹司還無倦意,順著她的意將防風燈罩裡的火苗吹滅,室裡陷入一片漆黑。適應了眼前黑暗後,隱約可見炕上人影。
若非那次替她包紮傷口,他不會懷疑她的性別。細看她五官,是真有些雌雄莫辨,然而行為舉止卻粗率颯爽地一如男人──有時比男人還要男人。
但她是名副其實的女兒身。
思及此,沖田鷹司臉上突然熱了起來,心頭也熱了。再想一遍她的面容,忽地覺得她長得也不十分陽剛,怎麼瞧就是有幾分女兒家的味道──很嗆人的味道。
為何要女扮男裝?她說還不是告訴他的時候,他可以不再多問,卻難不去猜測可能的原因。
黑暗中視覺受到影響,反之聽覺與嗅覺敏銳度倍增。他隱約嗅到一股暖中帶冷的香氣,極淡極清。
是女人天生的體香。
心頭一動,若有似無的香氣侵得他一夜無眠。
他沒注意到,始終背對著他的人亦一夜未睡。
她那時是怎麼說的?她說憑現在的他要探聽她女扮男裝的祕密還不夠資格,但只要他輸給師父,她就會告訴他。
他輸給師父了,因為猶豫。終究是最敬愛的師尊啊。
一敗之後,心情沮喪紊亂,忘了她還欠他一個答案。等到想起之時……
他已經死了。
*
「你在想什麼?都想得出神了。」
沖田鷹司回過神,看著走到身旁的殷良。
她還是一樣的男子打扮,一身清沁的藍,深的、淡的,像一池河塘,深的水色,淡的荻花。
唯一不同的是聲音,臨終之時亦不曾聽她嗓音有何改變,還當她的聲音就是那麼低沉渾厚,這對喬裝成男人倒是項不錯的利器──豈知,仍是假的,她原本的嗓音雖非鶯燕之語,卻同人一樣沉穩冷靜。
沖田鷹司微微一笑,「我想起了以前的事。」目光又投向眼前這一叢茂盛的岸邊荻花。
以前──生前。
他死了,來到苦境的死後世界──虛清之界,茫惘之後,就是等。
等她。
他在死魂必行的黃泉路盡頭一個白衣女子身旁靜坐,那女子總會吹簫,兩人未有交談,他感覺她亦在等人,不知已等了多久時候。
人,生前要等,死後也要等。
他很快就見到她了,不知該悲該喜。他擁住她,撫著生前沒有機會親近的臉龐;她一笑,難得地順從,將頭枕上他的肩。
終是可以在沒有立場對立的世界相守了,虛清之界住了許多不想投胎的死魂,在此過著和平安樂的日子。
殷良順著沖田鷹司的視線看向那初生淡雅藍紫的荻花,道:「是想起普生大師,想起東瀛,或者其他?」
「我想起妳。」
「哦?」殷良一奇,揶揄道:「原來生前的我比現在的我更值得懷念,人相處久了會感到厭煩就是這麼回事嗎?」
「呃,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沖田鷹司忙道。
殷良哈哈一笑,道:「你想起我什麼?」
沖田鷹司頓了頓,道:「以前我曾問妳為何要女扮男裝,妳說我進度不夠,又說輸給師父就要告訴我,現在條件達到了,妳的答案呢?」
殷良撫了撫下巴,認真道:「後者條件是達到了,不過進度有待商榷,我還是繼續保留答案吧!」
「如果我一直達不到妳心中進度的標準,妳就不跟我說了?」
殷良笑道:「也許,我們投胎之時我就會告訴你了。」
沖田鷹司身子一震,默然失語,片刻才道:「妳……妳想投胎了嗎?妳已經厭倦和我在一起了嗎?」
死魂的未來有兩種選擇,一是留在虛清之界,過著如同活人的生活;二是上「迴苦峰」投胎回陽世。留在虛清之界,他可以一直看著她,可若投胎,據迴苦峰那對引渡死魂的小兄弟說法,投胎後是全新的人生,前世如何,俱難成為來世之憑。
投胎,意味著分開。
殷良淡笑道:「虛清之界安詳和樂,待上一陣子是好,但,長久並不適合我,太無趣了。」
「但若是投胎,我們……」是心焦,怎能不擔心?
目光遠放,殷良臉上是灑脫的笑,「新的未來,就該活個新的模樣。」
沖田鷹司看著她的側顏,挺直的鼻象徵她的堅毅。
「妳不在乎嗎?」
「到時我已不是殷良,你也已不是沖田鷹司,不若前生的際遇和個性,來世的你我對現在的你我來說只是同質異貌的陌生人,如何能肯定來世還會互相吸引?」
沖田鷹司默然,是明白她個性的,她本就不是只會眷戀前世今生、只眷戀男女情愛之人。可是他也學不來她的瀟灑。
「但這裡是難得的無立場世界。」他說,試圖挽留一點什麼。
殷良轉頭看著他,深笑:「這就是為何我還留在這裡的原因啊。」
沖田鷹司心中一動,注視她那雙明亮的眼。
「現在的殷良和現在的沖田鷹司能夠常相左右,這才是我們的本願,不是嗎?」她的笑,微微帶著溫柔。
他動情地伸手去觸撫她的臉頰,問:「妳的一陣子是多久?」
「你想在這兒待多久,我的一陣子就是多久。」
沖田鷹司上前一步,將她摟住。
身旁的荻花田,因柔情而輕輕擺盪。
*
虛清之界有許多苦境沒有的美景,既珍且奇,他們初到之時先以一處為定居,但殷良總愛出外蹓躂,兩人索性離開原先居住之地,一同賞玩這個世界。
入夜了,兩人行在山間,不及下山,便尋了個山洞充當過夜之處。山洞並不深,入洞左首是條短道,連接另一個更大一些的窟洞。
他們進了內洞,在道口升了一堆火,就著火光,沖田鷹司覺得殷良看來比平時更溫和。
「妳什麼時候才肯嫁我?」
殷良咦的一聲抬起眼,「我們同吃同住,還不像夫妻嗎?」
「總是需要個名份。」他希望旁人問起時,他可以回答她是他的妻,而非得到曖昧的笑容。
殷良輕嘖兩聲,「原來你是那麼渴望名份的人?」
沖田鷹司道:「沒有名份,做任何事似乎都名不正言不順。」
「怎麼這句話在親熱時你又不說?」是促狹地笑。
「呃!」沖田鷹司語塞,微感不自在,「妳──妳的話──唉,妳的話總是教我難以反擊。」
言辭不僅犀利,有時更是大膽。
她的臉湊近,沖田鷹司心跳漏了一拍,敏感地嗅到一股淡不可聞的香氣。殷良嘴角噙笑,在他的唇上一吻,眼裡透著挑逗和戲弄,貼著他的唇低語:「名不正言不順的親密,你還要嗎?」
沖田鷹司的動作比言語上的回答更快,抱住她,吻住她,像一頭獵鷹找到了獵物,是自己的就不放手。
殷良熱烈地回應,兩人唇舌糾纏,吻啃對方耳頸,解褪彼此衣衫。
沖田鷹司忘情地嗅吻著她的肩,不論她外在打扮多麼似假還真,她的膚感、她的身段、她的味道,依舊是女人特有的柔軟與清香,讓他無法自持。
衣物已褪至腰間,露出他精健的體魄,沖田鷹司將殷良放倒,解開她腰巾,攤開她的衣服為墊。她身上有些傷疤,都是生前戰鬥中所傷,他細吻著那些不規則粉紅,又是憐惜,又感激情。
驀地,一線理智竄入沖田鷹司激盪著情慾的大腦,像受了驚一樣──抱著她的手臂感受到地上是那麼地粗礪,即使隔著一層她的衣服仍可摸出不規則的岩石凹凸。他翻過她的背,已磨擦得滿是紅痕,有些滲著血點。
愛慾交織的殷良完全感受不到背上刺痛,亦或不予理會,只是熱情地攀附著他。他忽停了動作引得她睜開迷濛的眼,問道:「怎麼了?」
沖田鷹司沒有回話,只是輕撫她背上紅腫。
殷良腦筋一轉,知道了原因,修長的指頭刷上他結實的胸膛,輕笑:「怎麼你做事只做一半的毛病會發生在這種時刻?」
沖田鷹司在她臂上輕咬一口以示此語的懲罰,道:「地上太硬。」攬著她一個翻身,將她換到自己上面。
殷良坐在他腹上,先是一怔,隨即揚唇一笑,俯身熱吻他,繼續方才未完的歡愛。
熾烈的律動中,兩人俱已沁出薄汗,沖田鷹司扶著殷良滑膩的腰,視線沒有稍移地瞅住她的面容。她緊皺著眉,咬著唇發出悶哼。
他手下一個用力,讓殷良暫停了動作,她喘著氣不解地看著他,沖田鷹司坐了起來,吻著她泛著齒印的唇,低語:「別忍著。」
坐在他腿上似乎有了憑靠,殷良半伏在他肩頭,在他的引動下再赴一場繾綣糾纏。
密實的兩具身軀已分不出誰是誰,粗喘呻吟是熱烈情潮的誘引。
沖田鷹司緊緊地抱著殷良,緊密的肉體摩擦不僅在他身上喚起強烈的歡愉,更在他心裡撞擊出滿溢的感情。
他啞嗓低喚:「荻。」
「嗯?」她氣虛地隨口回應。
「愛してるんだ。」
「什麼意思?」她問,聲音同樣沙啞。
他看著她滿臉薄汗,明眸朦朧,唇豔欲滴,長髮披垂,縱使從未見她著過女裝,不知是何嬌態,但他已發現她最女人的一面。深情一笑,道:「愛妳之意。」
殷良又是一怔,怔得比方才久了些,是沖田鷹司的探動召回她的神智,然後,一抹笑在她臉上蕩樣開來,既美,且柔,是他眼中最動人之景。
殷良癱在沖田鷹司身上,累倦得幾乎要睜不開眼。一個翻身,想躺到旁邊去,大手一攬,身下又是熱燙的鐵軀。
「熱。」她低吐一字,卻懶得再作掙扎,閤眼便睡。
沖田鷹司摸了摸兩人身上汗膩,從褪在一旁的衣堆裡掏出一條絲巾──她為他裏傷的那條,輕柔地拭抹她身子。
睡顏無憂,長髮垂攏,她著男裝的理由已不重要,在他眼裡,男裝是她的一部分;在他生命裡,她是他血肉相溶的連繫。
他擁著她睡著了,直到被她翻身的動作弄醒。
「天亮了嗎?」她半瞇著眼含糊問道。
沖田鷹司順著道口看去,外頭昏白一片,天亮了。但他伸手遮住她的眼,低聲道:「還沒,繼續睡吧。」他想再多抱她一會兒。
殷良自已見到外頭光線,卻由得他扯小謊,閉上眼。
反正又不趕路。
(完)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